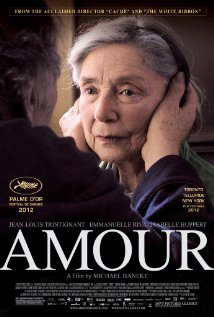《和山姆一起上學去》(Including Samuel)的導演叫丹哈比(Dan
Habib),他的小兒子山姆(Samuel)有腦性麻痺。雖然智力無礙,但永遠沒法自己站起來,更不能好好的控制肌肉。丹哈比把山姆在學校接受教育的情況拍下來成了這部紀錄片,拿下了北波士頓影展最佳紀錄片跟國際殘疾人組織年度最佳正面影片大獎。
為什麼影片的名字叫《Including Samuel》呢?原因是指這部紀錄片裡山姆所接受的教育叫 Inclusion
Education(融合教育)。這種教育的宗旨是殘疾人仕應該跟一般人一起接受教育而不是讓他們在特殊學校裡上課。有這種融合教育思想的教育家甚至反對
特殊學校。我邊看邊拍手,這真的是個很捧的想法。
一直都不是很喜歡殘疾人仕集中起來受教育的形式,總是覺得我們的社會又不會把殘疾集中起來上班,為何讀書要把他們集中起來。學校教育本來就應該是社會的縮影,地球上本來就有各種人,為什麼讀書時要把他們隔離,出社會就要規定公司要請一定比例的殘疾人仕呢?
紀錄片最捧的地方就是訪問了很多山姆的同學,童言童語的,十分可愛。班上只有山姆是殘疾學生,但每個同學都很喜歡山姆啊!小朋友的心最單純了,跟伊甸園裡的亞當與夏娃純潔像白紙一樣,沒有正常與不正常的分別。要是小朋友有:「那個人是殘疾人仕啊!」的想法,一定是父母教的。不然,他們怎麼懂得去分別呢?老實說,如果從來沒發明過「殘疾」這個詞,我們又怎會有殘疾這個觀念呢?又如果我們的小朋友從小身邊就有殘疾人仕的同學,長大後又怎會有歧視呢?所謂的和諧社會不就是能容許跟自己不同的人一起生活嗎?要是我有小孩又有這種學校的話一定要他去唸,長大後心胸一定會比較廣寬。(這種類似的議題在去年中的台北錦安里事件討論過了,詳見:http://straitsperspective.blogspot.tw/2012/07/blog-post_21.html)
當然這種融合教育需要很多資源,像紀錄片中的山姆,有個助教老是陪著他。到底社會要不要投資在殘疾人仕上呢?這就是正義的問題,要找Michael Sandel 來問一下了。但我認為,殘疾人仕畢竟不是多數,而投放多一點資源讓大家能多接受不同的人,這是值得的。
最後,不得不提一下,每次《主題之夜》都會請嘉賓來參與討論,當天請的是吳武典老師。吳老師是台師大特教系的名譽教授。他最後說到,在特教系裡殘疾學生是叫「特殊需要學生」的,因為他們只是比別人有特別的需要。他說:「每一個人,在某一個時間,都會有特殊的需要。」我覺得這說得太好了,我們現在每天跑跳無礙,思想轉速飛快,永遠等不了轉速慢的人。總是覺得轉速慢的人妨礙地球轉動。卻沒想到一天自己會變老,變慢,到時就有年青小伙子嫌棄我們慢。如果我們從小就受「這個世界有各種人,這才叫正常!」那不是更好嗎?